男女主角分别是朱标朱元璋的现代都市小说《精品推介朱元璋被我说得退位让贤了》,由网络作家“山泽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《朱元璋被我说得退位让贤了》,是作者大大“山泽”近日来异常火爆的一部高分佳作,故事里的主要描写对象是朱标朱元璋。小说精彩内容概述:说句准话!”“你到底愿不愿意给孙妃服丧?”“不愿意!”朱标梗着脖子,昂着脑袋,坚定回道:“我身为皇室嫡子,大明储君!”“能让我身披麻衣、服丧吊孝的只有你和我娘。”“你和我娘活得好好的,我给谁服丧?我服丧做甚?”“难不成咒您早点驾崩,我好早日登基?”此时老朱被气的眼冒金星,......
《精品推介朱元璋被我说得退位让贤了》精彩片段
洪武七年。
应天皇宫。
此时一名中年嘴里不停叫骂的同时,举着长剑便朝面前青年追着砍去。
而那青年虽不似中年魁梧,可动作却是异常灵活。
始终与中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安全距离.......
“臭小子,你给咱站住,看咱不砍死你!”
中年正是推翻暴元,再造华夏的洪武皇帝朱元璋。
而他高举宝剑,扬言要砍死的青年。
则是历史上地位最为稳固的太子,也是明初的二皇帝,太子朱标。
“小杖则受,大杖则走。”
“爹,我又不傻!您举着大宝剑,我能站着不动让您砍?”
“有本事您换成小木棍儿,我保证不跑!”
“你小子......”
听到朱标非但没有认错,反而还一再拱自己的活。
此时正扶剑喘气的朱元璋顿时感觉火冒三丈,再次举起长剑便又追了上去。
而看到老朱再次上前。
朱标同时逃跑。
依旧和老朱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安全距离,遛着老朱在庭院中锻炼身体。
半晌。
见老朱累得气喘吁吁,额上也满是汗珠。
朱标轻笑一声,这才冲老朱沉声喊道:
“爹,孙贵妃薨逝,让我服丧本就不合礼制。”
“士大夫以上,庶母死,嫡子不需服丧,这是礼制,这是规矩!”
“就因为你宠爱孙贵妃,如今她薨逝,竟然让五弟守孝三年,还让我这个太子给她摔旗扶杖,为其服丧。”
“您这不是凭一己好恶,乱法违纲吗?”
“商纣宠信妲己,周幽王痴迷褒姒,历史血的教训就在眼前?”
“难不成您想在史书上再添一笔,让后世之人都知道,您这个洪武皇帝宠信后宫,乱法违纲?”
“你......你拿咱和商纣、幽王作比?”
老朱被气的脸色煞白,浑厚嗓音甚至有丝丝颤抖。
可饶是如此。
朱标依旧不肯罢休,直视老朱那愤怒的双眸,厉声喊道:
“与商纣、幽王作比,您也有所不及!”
“他二人都是承继父位,不知开国创业之艰辛,纵然昏聩也情有可原。”
“而您!筚路蓝缕,披荆斩棘,十数年这才驱逐暴元,重整汉人天下。”
“如今天下初定,您又深知创业艰辛,此时竟还能为一后宫妇人做出违反纲常之事,您岂不是比商纣、幽王更加昏聩!”
“怎么?您觉得如今大明安定,您便能高枕无忧?”
“还是说你打算学唐玄宗,半生勤政换半生昏聩?”
“不然儿子也学学肃宗李亨,来一场马嵬兵变,让您进位太上皇?”
“混账.....混账东西......”
听到朱标一再拿他与历史上宠信后宫妃嫔的昏君相比,老朱气的差点背过气去。
他何时因为宠信后宫妃嫔耽误国事了。
他只不过是觉得大明初定,孙氏还未享尽荣华便轰然早逝。
心中亏欠,这才让朱标以及众皇子为孙氏服丧。
怎的他的这一点恻隐之心,在朱标眼中竟成了宠信后宫的罪证。
“小子,你....你给咱说句准话!”
“你到底愿不愿意给孙妃服丧?”
“不愿意!”
朱标梗着脖子,昂着脑袋,坚定回道:
“我身为皇室嫡子,大明储君!”
“能让我身披麻衣、服丧吊孝的只有你和我娘。”
“你和我娘活得好好的,我给谁服丧?我服丧做甚?”
“难不成咒您早点驾崩,我好早日登基?”
此时老朱被气的眼冒金星,偏偏他还想不出半句话来反驳朱标。
“臭小子,你敢咒咱.....”
怒吼一声,朱元璋再次举起长剑便要朝朱标砍去。
只不过这一次。
朱标非但没有继续逃跑,反而上前一步,梗着脖子冲老朱威胁道:
“老爷子,有话说话,你要再追,我可就不跑了!”
此话一出。
已经迈开一条腿的朱元璋顿时僵在了原地。
他是被朱标气的不行,可还远没有到失去理智的地步。
毕竟三尺青锋在手,万一朱标不跑,真的伤到朱标那还了得?
就在老朱左右为难,不知如何下台之时。
只见门口人影闪动,老朱当即怒声吼道:
“谁在那边,给咱滚进来!”
话音落下。
李善长、胡惟庸怯生生走了进来。
“臣参见陛下,参见太子。”
“哼~”
老朱冷哼一声,看向李善长怒声喝道:
“李善长,亏你还是太子少师,就知道躲在门口看戏,不会上前拦住咱?”
“万一咱伤到太子怎么办!”
听到这话。
李善长表情尴尬,很是为难的耷拉着脑袋。
刚刚老朱与朱标的动静,他可是听到了一二。
明明是老朱自己说要砍死朱标,怎么朱标不跑,他还不乐意了。
而且现在还怪自己没上前阻拦。
就刚刚那架势,除了马皇后,谁敢阻拦老朱不都是个死?
就在李善长心中无奈苦笑之时,朱元璋再次训斥道:
“咱让你教导太子,你竟然教出一个顶撞君父的太子!”
“罚俸!罚俸半年,降职一级!”
见老朱将怒火倾泻到自己身上。
李善长更是有苦难言。
你们爷俩斗法,怎么遭殃的却是我。
尽管心中腹诽。
可当意识到老朱的矛头尽在自己身上,根本不理会旁边的太子朱标。
李善长心领神会。
顺势便接过了老朱手中的长剑。
“陛下息怒,太子一时莽撞,稍加劝诫即可。”
当看到老朱瞥了眼不远处的朱标。
李善长旋即看向朱标恭敬说道:
“太子殿下,礼制之事权且放在一边,然君父之命可是万万不能违抗的。”
“若是因此事伤了你与陛下父子之间的感情,那岂不是得不偿失?”
见朱标根本不理会自己。
李善长心下一定,状着胆子继续说道:
“殿下,您看是否能给陛下致歉.....”
就在朱元璋、李善长以及旁边的胡惟庸都以为,太子朱标当着他们的面,会多少顾及老朱的帝王颜面,暂且给老朱认错之时。
只见朱标猛地一甩衣袖,当即背过身去。
“五弟近来功课繁巨,这几日孤不会让他出门。”
“还有其他皇子,均不得外出!”
“父皇要把孙贵妃的丧事办的如何隆重,儿臣不管!”
“哼~”
朱元璋冷哼一声,既没承认也不否认。
洪武四年。
当时朱元璋想让刘伯温出任中书省左丞相。
皇帝亲自降恩,这对其他大臣来说本是求之不得的事情。
可刘伯温听后却一再推脱,甚至还提出要告老还乡。
好像在刘伯温看来,当他老朱家的官儿就压根没有善终。
好像在刘伯温眼中,他朱元璋是个只能共苦,不能同甘的寡义帝王。
直到现在。
一想到刘伯温当时那副唯恐避之不及的惶恐模样,老朱还是气不打一处来。
“重八,我问过标儿了,弹劾刘伯温的折子无非是说他贪污受贿,结党营私。”
“可刘伯温什么性子你是知道的,他的清高是骨子里的,他怎么可能做出这些贪赃枉法的事来。”
“哼,清高,他清高的很!”
“就是因为他清高,咱才要借机好好敲打敲打他!”
朱元璋当然知道涂节等人弹劾刘伯温乃是诬告。
朱元璋甚至还知道,涂节等人弹劾是胡惟庸授意。
而胡惟庸之所以如此,乃是为了那左丞相之位。
可朱元璋就是要借故敲打一下刘伯温。
哪怕得知刘伯温要上京请罪,朱元璋也并未下旨让其安心。
“重八,我当年答应过刘伯温.....”
“妹子,这事儿不提了!”
不等马皇后说完,朱元璋直接冷声打断。
“你当年怎么答应刘伯温的,咱事先可一点都不知道。”
“咱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,才让他告老还乡的。”
“这一次是他自己要进京请罪,不是咱下令让他来的。”
“他不是觉得在京都没有善终吗?”
“咱就让他留在京都,咱就给他个善终!”
“他不是担心鸟尽弓藏吗?咱就是要让他看看,看看咱朱元璋是不是兔死狗烹的寡义君王!”
“就算是死,咱也要让他死在京都,让他一直待在咱眼皮底下!”
对于其他大臣,朱元璋自然没有这么大的火气。
或者说其他大臣根本没有资格让朱元璋动怒。
可唯独刘伯温是个特例。
无论是因为刘伯温出身世家,先前乃是地主老爷。
亦或是刘伯温的身份,乃是朱元璋最讨厌的士子领袖。
甚至因为刘伯温的弟子杨宪,彻底欺瞒了朱元璋。
总之朱元璋对刘伯温这样一个,为大明开创立下汗马功劳的谋臣,始终有些不满。
用老朱的话来说,就是不交心!
而且刘伯温骨子里的那份清高,甚至让朱元璋觉得这老小子瞧不上自己!
而看着朱元璋那一副傲娇且固执的模样,饶是马皇后也觉得有些棘手。
无奈之下,马皇后只好问道:
“那明日朝会,你打算如何处置刘伯温。”
“嗯.....”
朱元璋微微一顿。
想到朱标关于刘伯温的安排后,心中怒火莫名消减了不少。
“原本咱打算明日朝堂上,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好好敲打敲打刘伯温。”
“可是老大刚刚下令,让刘伯温好生休养。”
“咱也不想驳了老大的面子。”
“只不过这一次,就算刘伯温不当咱朱家的官儿,咱也要让他留在京都!”
听到这里,马皇后这才安心不少。
尽管她也已经看出来,老朱还在生刘伯温的气,老朱也是故意折腾刘伯温。
可此事交给朱标,一切便都好说了。
毕竟和老朱相比,朱标还是更讲道理的.....
夜幕刚刚落下。
老朱便迫不及待,只身一人前往太子东宫。
毕竟白天他刚拿着剑追砍朱标。
万一朱标多想,让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出了嫌隙反倒不好。
等到了太子东宫。
老朱没有让下人的通报,反而自己一个人径直朝亮光的房间走去。
“兄长,今天白天你好像一再催促李善长告老还乡?”
听到里面朱标正和常氏议论朝政。
老朱脚步微顿,站在柱子旁竖起耳朵开始偷听。
“不错,我是一再催促李善长告老还乡。”
“可是李善长有什么做的不好?”
朱标放下手中折子,伸了个懒腰后,缓缓说道:
“李善长做的很好,虽然私下有些小心思,可他在丞相之位上也还算称职。”
“只不过父皇不久之后或许要裁撤丞相。”
此话一出。
和常氏一样,门外的朱元璋也不由身体一颤。
他的确有意裁撤丞相,可他只不过是有这个念头而已。
哪怕是对朱标,他也从未提及过。
按理说,朱标应该不知道才对啊。
“兄长。”
就在老朱诧异之时,屋内的常氏继续问道:
“兄长,丞相制度已传承千年,父皇为何会裁撤啊?”
“还不是父皇圣心独断,不愿相权分割皇权。”
朱标叹了口气,有些无奈说道:
“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这权力着实太大了些。”
“而且如父皇这样的人,是绝对不允许百官之中再出现一个小皇帝的。”
“不过话说回来,父皇裁撤丞相,也是担心后世出现奸相欺国的事情。”
朱标一字一句,都切切实实说中老朱心中所想。
可就在老朱认为朱标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。
打算推门进去,和朱标仔细商议该如何裁撤丞相制的时候。
只听房内的常氏再次开口。
“所以,兄长你一再催促李善长告老还乡,是防止.....”
常氏有些为难,没有继续说下去。
可朱标明白她的意思,紧跟着说道:
“不错,让李善长尽早告老还乡,是防止他给丞相制度殉葬。”
“刚才你也说了,丞相制度传承千年,父皇想要裁撤这个制度,必然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。”
“那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借口,无非就是当下大明的丞相欺上瞒下,弄权坏国。”
“除此之外,恐怕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借口了。”
虽然常氏也觉得朱标所言有理。
可在她印象中,朱元璋不是个会屠戮功臣勋旧的皇帝才对啊。
“兄长,我记得有一次你与父皇谈及古代帝王时。”
“父皇最为推崇汉高祖刘邦,可对刘邦屠戮功臣的事,父皇却是嗤之以鼻。”
“父皇应当不会是屠戮功臣的帝王才对啊。”
“而且父皇还给功勋武将都发了免死铁券,想来父皇不会像汉高祖刘邦那样,屠戮功臣吧!”
(历史上朱元璋的确说过,具体是明实录还是那本书,作者忘记了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绝对不是从营销号上看到的)
常氏这番话在朱标听来,甚至有些可笑。
要知道,洪武大帝杀起功臣来那可是绝不手软的。
而且一旦动刀,就是几万,十几万,几十万的人头滚滚。
只不过常氏说得也是没错,老朱的确曾对刘邦屠戮功臣嗤之以鼻。
“父皇是说过这话,可那时候是在开国之初。”
“当时大明刚刚建立,百废待兴。当时的父皇也是踌躇满志,一心想的是如何建设大明。”
“恐怕父皇自己都想不到,有朝一日他也会像汉高祖刘邦一样,成为一个屠戮功臣的帝王。”
废除丞相制的时候,因为马皇后和朱标都还在,老朱还算仁慈。
没有屠杀太多大臣。
可等到皇权交替之时,老朱杀起功臣来,那是眼皮都不带眨的。
譬如历史上的蓝玉案,从审理到结案,用了仅仅不到半月的时间。
这摆明了就是朱元璋要为儿孙开路。
“至于你刚才说得免死铁券.....”朱标轻笑一声,玩味说道:“这不过是彰显皇恩浩荡的手段罢了。”
“若大臣真觉得免死铁券能够免死,那他们才是离死不远了。”
砰~
朱标话音刚落。
只见朱元璋一把推开房门,直冲冲走到朱标跟前。
也是见老朱摆出一副吃人的架势。
朱标冲常氏微微示意,让她离开,屏退门外宫人。
就在常氏前脚刚踏出房门的瞬间,只听老朱一掌狠狠拍在案桌上,冲着朱标怒声吼道:
“刘伯温那臭腐儒觉得咱是薄情寡恩、屠戮功臣的无义君王也就罢了。”
“没想到你竟然也是如此看咱!”
“咱还想着让刘伯温待在京都好好看看,看咱会不会屠戮功臣。”
“可是没想到!咱的儿子!咱大明的太子!竟然也觉得咱是屠戮功臣的寡义君王!”
见朱标应了一声,步履轻快朝殿外走去。
马皇后一头雾水之下,忙拦住朱标开口问道:
“标儿,你说的替罪羊是....”
“替罪羊正是胡惟庸啊!”
朱标笑着解释道:
“如今父皇提拔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,胡惟庸坐镇中书省,他的学生涂节主管御史台,说是胡惟庸把控朝堂也不为过。”
“所以设置锦衣卫,包括胡惟庸在内的所有官员都知道,锦衣卫就是针对胡惟庸来的。”
“也是因此,若是朝中官员反对之声过于强烈,不管是不是胡惟庸暗中指使,父皇都可以将所有罪责怪到胡惟庸头上。”
“娘,胡惟庸可是个难得的聪明人,这点道理他自然能想明白。”
“所以为了防止百官反对之声过于强烈,引得父皇震怒,胡惟庸必然要先行劝解反对设立锦衣卫的官员。”
朱标看了眼笑容满面的朱元璋,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“所以我和父皇只需安静待在宫中,自然有胡惟庸去处理那些麻烦声。”
“而那些反对设立锦衣卫的声音,恐怕都传不到我们耳朵里。”
“不对,标儿,这点你说的可不对!”
朱标刚一说完,老朱便笑着补充道:
“设立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,毕竟是有些上不了台面。”
“若是听不到一点反对之声,那胡惟庸岂不是不打自招,证明自己已经彻底掌控朝堂所有官员吗?”
“对对对,娘,我爹说的对。”
朱标顺着老朱的意思,继续说道:
“若是没有一点反对的声音,那就是胡惟庸把控朝堂,罪当论斩。”
“若是反对之声太大,那便是胡惟庸暗中授意,想要对抗皇权。”
“至于这件事具体的程度,就让胡惟庸自己去把握吧。”
听朱标说完,马皇后也跟着笑了摇头道:
“你们爷俩啊,就可着胡惟庸一个人霍霍!”
马皇后也知道胡惟庸是个难得的聪明人。
可在老朱和朱标这对父子面前,纵然胡惟庸再聪明也无济于事。
胡惟庸恐怕做梦都想不到。
他得到了心心念念的左丞相之位,实际上却只是老朱和朱标计划中的一环罢了。
胡惟庸任职左丞相期间,诸如这次设立锦衣卫,他自然要顶在百官前面,替老朱安抚官员。
而等活着的胡惟庸没有利用价值,那老朱和朱标也就该借由他的死,彻底废除宰相制。
眼下情形,胡惟庸就好像是一个聪明的糊涂蛋。
看似得偿所愿,大权在握,可实际上却依旧在老朱和朱标的股掌之间。
只不过马皇后对胡惟庸却没有半点同情。
毕竟胡惟庸只是个棋子,老朱和朱标才是大明的执棋者。
棋子的作用就是被执棋之人利用。
若是死也能为整个局面做出贡献,那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
只不过想到朱标的心思竟也如此深沉,马皇后不免有些忧虑的看向朱元璋。
“重八,标儿智谋深远,可终究还是个少年人,他的老成似乎和他年纪有些不太匹配。”
“嗯.....”被马皇后这么一说,老朱也不免紧张了起来。
“妹子,你是说.....”
“多智易夭,慧极必伤。”
“我知道不该说这丧气话,可标儿刚刚二十岁,心思沉稳比之一些老臣都不遑多让。”
“重八,找个机会让标儿休息休息吧。”
看着马皇后一脸关切的样子,老朱很是认同的点了点头。
毕竟老朱也知道慧极必伤的道理。
历史中但凡聪明绝顶之人,便少有长寿之人。
此话一出,老朱瞳孔微缩,盯着常氏连忙说道:
“丫头,你说清楚些。”
“是!”
常氏深吸口气,继续说道:
“兄长监国理政多年,深知勋贵武将多有不法。”
“兄长也多次告诫过他们,可这些人不过是安生个十天半个月,之后便又为非作歹起来。”
“对于这点,兄长很是头疼,有时甚至还打算杀一两个人,以正视听。”
“所以兄长认为父皇会斩杀功臣勋贵,并非兄长认为父皇乃是过河拆桥的无义君王,实在是兄长认为这些勋贵武将逼的父皇不得不严惩。”
此时朱元璋心头陡然一惊。
他自然清楚大明开国以来,勋贵部旧多有不法。
特别是洪武三年,赏赐给他们丹书铁券之后,这些勋贵部旧愈发无法无天。
譬如强占百姓农田,欺压良民,甚至劫掠民女的事都时有发生。
因此在洪武五年。
老朱亲自撰写《申诫公侯文》,还命刑部打造铁榜,上书九条严惩之法,为的便是敲打那些勋贵部旧。
可是老朱也很清楚。
无论是他亲自撰写的《申诫公侯文》,还是打造的铁榜,最终都是收效甚微.....
“丫头,你刚刚说老大也想找出一两个典型出来,杀一儆百?”
“是!”常氏郑重点头,“太子也对勋贵部旧多有不满,太子也认为应该杀一儆百,震慑其他勋贵部旧。”
“父皇,勋贵不法,臣妾也有所耳闻。”
“难道按我大明律法,严惩勋贵部旧,也能算是兔死狗烹吗?”
“难不成那些开国功臣犯我大明律法,也要姑息不惩吗?”
“臣妾虽不懂什么朝政大事,可臣妾父亲在时治军极严,若有违法军法者,哪怕是副将亲信也要依照军法论处。”
“难道仅凭这点,就能说臣妾的父亲也是过河拆桥之人吗?”
常氏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。
杀勋贵武将,那是这些勋贵武将自己作死,逼得老朱不得不动刀。
和什么鸟尽弓藏,兔死狗烹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最起码。
在马皇后未死之前,朱元璋所杀的那些勋贵武将,都是他们乱法害民自己作死。
见常氏说得有理有据,朱元璋眼前一亮。
对自己这个儿媳也是愈发喜欢了起来。
“看吧,老大监国多年,又怎会不懂你的心思?”
“老大又怎会认为你是兔死狗烹的无义君王。”
被马皇后这么一说,朱元璋有些尴尬的点了点头。
不过见常氏还在,老朱忙躲开话题,继续问道:
“丫头,那你可知老大准备拿谁开刀?”
“这....”常氏眉头微皱,想了好大一会儿后这才说道:
“兄长对永嘉侯朱亮祖、德庆侯廖永忠似乎多有不满。”
“臣妾也不敢断言,只是听兄长的意思,好像这二人做事最为荒唐。”
“廖永忠吗?”
老朱低声喃喃,当即便明白朱标此举的弦外之音。
无论朱亮祖、廖永忠,还是其他开国功臣,但凡朝廷要追究,他们哪一个都有杀头的罪过。
朱亮祖自然不必多说,为人鲁莽、蛮横,在天下未定之前是个悍将,可在大明建立之后便是个祸害。
至于廖永忠....
老朱相信,朱标拿他开刀定然有别有深意。
毕竟当年正是廖永忠护送小明王韩林儿,后来什么样的结果所有人都知道。
船只沉江,韩林儿溺水,廖永忠精通水性,安然无恙。
甚至老朱还曾听闻。
一次酒醉,廖永忠竟说是他朱元璋下令溺死了韩林儿....
“嗯,回去告诉老大,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”
“而且不必考虑的太过周全,就算他把天捅出个窟窿,咱也能帮他补上!”
朱元璋面沉似铁,当即冷声喝道。
只不过下一秒。
当注意到马皇后和常氏都用奇怪的眼神看向自己时。
老朱顿时感觉有些难堪。
“咳咳,咱不是要屠戮功臣,咱也没想过卸磨杀驴,要处置跟咱南征北战的开国功臣。”
“常丫头刚刚不是说了吗。”
“是那些勋贵武将自己乱法害民,理应被国法绳之。”
“咱总不能为了保全自己善待功臣的名声,就姑息养奸,纵然这些勋贵武将继续祸害咱大明的百姓吧。”
“是呢,陛下!”
马皇后拖长嗓子,故作调侃道:“现在陛下不生太子的气了吧。”
“那是那是!老大说得没错,不是咱要杀功臣,是这些功臣自己犯法。”
“大明律法只惩处那些欺压百姓的人,和他们是否是开国功臣没有关系。”
语罢,老朱看向常氏振奋说道:
“常丫头,你回去告诉标儿,让他继续帮咱理政。”
“这....”
当看到常氏有些犹豫,朱元璋当即拿出长辈的姿态,故作威严道:
“怎么?丫头你不愿意?”
“不是不是!”
常氏连忙摇头否认,“臣妾没有不愿,只是臣妾以为,父皇应该当面和兄长说清楚。”
“兄长还有.....”
“对!”
不等常氏说完,旁边的马皇后也跟着说道:
“就应该你自己过去。”
“你也不想想,本来你去太子府是为了什么?”
“怎么事儿没办成,反而给标儿头上开了个洞!”
被马皇后这么一说。
老朱自觉理亏,起身慢悠悠朝殿外走去。
“咱.....咱当老子的,怎么能给儿子赔不是。”
“咱告诉你们哈,咱不会去给找老大赔不是。”
当走到殿门口,老朱转头看向马皇后道:
“妹子,你刚才不是说想吃碗白粥吗?咱现在命人去给你做。”
尽管老朱的借口很是蹩脚,但马皇后还是笑着点头道:
“是呢,多谢陛下了。”
闻言。
老朱大步流星便朝门外走去。
毕竟是他对不住朱标,上午还着剑追看朱标不说,晚上还给朱标头上砸了个洞。
就算不是去给朱标道歉,老朱也想看看朱标头上的伤是否有大碍。
而等老朱走后,马皇后看了眼老朱离开的方向,对着常氏出言调侃道:
“你们这位父皇就是爱面子,这不,去找老大赔不是,还要找个借口。”
“父皇要给兄长赔不是?”
见常氏一脸诧异的盯着自己,马皇后也不由一愣。
“不是你刚才说,要让你们父皇去找太子吗?”
“是啊.....”
常氏愣了一会儿,随即连忙摇头道:
“娘,儿媳怎么敢让父皇给太子赔不是啊!”
“儿媳刚才是想说,兄长正在寻找新的制度,好取代丞相制。”
“让父皇亲自去找兄长,也是觉得父皇和兄长有事要商议!”
被常氏这么一说,马皇后微微一愣,随即便直接笑出了声。
“不管他们,让这爷俩自己操心去吧。”
“丫头,你已经有三个月的身孕了吧。”
“先前徐叔大军驻扎的图拉河,距离蓝玉被围困的捕鱼儿海有近三百里的路程。”
“而方才军报上也说了,徐叔一日之内,先是攻破了图拉河的元兵,然后于午夜时分赶到捕鱼儿海,同蓝玉前后夹击,再次攻克捕鱼儿海的元兵。”
“因此儿臣可以断言,此次徐叔在意的是兵贵神速,所以大军绝不会 携带过多的粮草、辎重。”
“然而捕鱼儿海距离北平多达五百里,这五百里的距离,元兵可以在任何地方设下伏兵,拦截粮草。”
朱标的话虽然夸张了些,但也有几分道理。
因为北平以北的草原等地并不适合种植作物,就算勉强建设城池,也无法设立军屯,更没办法迁徙百姓,耕田自足。
因此。
无论是如今的大明,还是先前任何一个王朝。
对待北方草原部族,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扫荡。
也是因为没有城池的保护,北元到捕鱼儿海的这五百里路程中,元兵很容易穿插到任何地方,也可以在任何明军守备松懈的地方设置伏兵,劫掠粮草。
“父皇,一旦粮道受阻,大军军心必乱。”
“而徐叔领兵多年,自然也能看出其中端倪,所以儿臣断言,大军定不可能在捕鱼儿海久居。”
“加上北伐军中唯一一个可能贪功冒进的统帅蓝玉,也被儿臣召回。”
“其他统帅,无论是徐叔,还是表哥李文忠,宋国公冯胜,他们都不是轻敌冒进之人。”
“所以!”
“如果儿臣预料不错的话,等儿臣召回蓝玉的消息传到北伐大军后,徐叔定然会放弃捕鱼儿海,率领大军折返北平。”
嘶~
被朱标这么一说,老朱不由倒吸一口凉气。
朱标卓越的军事眼光自然让他震惊。
可更让老朱震撼的,是朱标下令召回蓝玉时,胡惟庸还没有把最新的战报送来。
如此说来。
朱标甚至一早便洞悉千里之外的战局。
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。
老朱扪心自问,哪怕是他也做不到朱标这种程度。
也正是发现朱标有一等将帅的军事眼光。
老朱突然觉得,或许等北方平定之后,大明便不需要那么多的勋贵武将。
毕竟朱标就是数一数二的军伍奇才。
念及至此,老朱眼眸闪过一丝冷厉,看向朱标沉声问道:
“标儿,如果现在是你当皇帝。”
“北伐大军一举踏碎元廷,活捉了元主,北方再无边患。”
“等大军凯旋之后,你又打算如何赏赐这些有功将帅,你又打算如何安置魏国公徐达?”
见老朱对徐达的称呼,从较为亲近的天德变成了魏国公。
加之此时浑身气势陡然冷厉。
朱标当即便明白了老朱的言外之意。
“父皇,就算北伐大军得胜还朝,儿臣依旧不会赏赐他们。”
“有功不赏,有过不罚,可非明君!”老朱语调深沉,说话的同时眼眸中闪过一丝冷意。
可即便如此,朱标依旧不想按照老朱预想的那般开口。
“父皇所言极是,有功不赏,有过不罚,并非明君所为。”
“所以儿臣便会让这些淮西将帅功过相抵。”
见老朱眼中闪过一抹疑惑,朱标深吸口气,沉声说道:
“先前儿臣已经说过了,淮西将帅素有不法行径。”
“因此,若是此次他们得胜还朝,朝廷便在他们抵京之前,将他们往日种种不法行径昭告天下。”
“简单来说,这些将帅在此次北伐中立下了多少战功,那他们不法行径的惩处就有多重。”
毕竟是自己的娘家人,对常茂、常升以及蓝玉,常氏还是想尽可能让他们远离争斗旋涡。
见朱标不语,常氏犹豫再三,冒着后宫干政的风险怯生生问道:
“兄长,朝政处置勋贵不法,当真要在北伐大军回京之后开始吗?”
此话一出,朱标好像被踩到了尾巴一样,瞬间紧张了起来。
见朱标如此,常氏当即便跪下请罪道:
“臣妾并无干政之心,只是...只是......”
“起来吧。”
没等常氏说完,朱标淡淡开口说道。
“如今父皇也是不愿处置不法勋贵,只是他们闹得动静太大了些。”
“淮西武将中,除魏国公徐达、表哥李文忠,以及中山侯汤帅之外,其他淮西勋贵或多或少都有不法行径。”
“若只是他们各自为营也就罢了,可这群家伙竟然相互勾结。”
“凤阳之地,朱亮祖、廖永忠二人合伙贪墨十户百姓田产。”
“杭州膏腴之地,耿炳文、费聚等七名侯爵合资开设青楼数间,强抢民女,逼良为娼,入府私用。”
“这些家伙以为法不责众,以为他们捆绑在一起,朝廷便会投鼠忌器。”
“甚至在他们北伐期间,其府中下人依旧匆忙敛财,欺压百姓。”
“这些家伙想干什么?以为把所有勋贵绑在一起,父皇便不会怪罪?还是以为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,朝廷便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?”
“蠢!他们这样,只会让朝廷收拾起来更加简单罢了。”
“捆在一起,甚至用不着审问他们的同谋者有谁!”
朱标属实是觉得这些勋贵有些看不清形势。
若是皇位上坐着的是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,他们捆绑在一起,或许会让皇帝投鼠忌器。
可他们忘了,如今皇位上坐着的,是贫民出身,深知百姓疾苦,深感百姓艰辛的朱元璋。
是那个鏖战千里,击溃各路诸侯,将北元蛮族驱逐出中原的洪武大帝。
面对朱元璋,他们如此捆绑,只会让朱元璋觉得他们想要联合起来对抗朝廷。
等雷霆之怒降下,对他们的惩处也是无差别的屠杀。
“常妹,如今父皇心中还有几分同袍之谊,趁此时将勋贵不法的事拿到明面上,父皇念及往日香火情,也会对他们网开一面,不至于让他们尽数死在大明律法之下。”
“可若是等他们越闹越大,届时父皇降罪,便不是简单惩戒这么简单了。”
常氏闻言,额上也惊出不少冷汗。
虽然老朱在她和朱标面前,始终都是一个宽厚的慈父形象。
可常氏自然不会忘记,他们面前的这位慈父,还是杀伐果断的洪武皇帝。
而且自己这位兄长,也从来不是一个心慈手软之人。
哪怕一切都尚未开始,可常氏几乎能够预见,这次惩治淮西勋贵不法的案子,势必要有不少人因此殉命。
“那....兄长,臣妾可否先一步返回娘家,仔细查明看看常茂、常升是否有不法行径.....”
“也是不急。”
“兄长可是担心北伐将帅得知消息,拥兵自重,甚至投靠北元,对抗大明?”
“倒也不是。”
常氏所说,若放在其他朝廷或许可能发生。
可这里是大明朝,那些淮西将帅虽不太检点,有很多不法行径,可他们对朱元璋的畏惧更深,对北元的仇恨更大。
因此就算把屠刀架在这些淮西将帅脖子上,他们也不可能叛出大明。
也正因如此,朱标才决心此时敲打他们一二,而不是将他们全部严惩。
“兄长所言极是,雄英尚未出世,刘先生便愿意收雄英为徒,臣妾自然要替雄英行拜师礼。”
常氏说着,竟直接半跪在刘伯温跟前。
见此一幕。
刘伯温连忙跪在地上,不敢受礼。
“太子妃身份贵胄,臣怎能受的起啊。”
“无妨无妨,这是常氏替雄英行的拜师礼。”
朱标说着便将刘伯温搀扶了起来。
可即便如此,刘伯温依旧不敢受礼。
惶恐之下,刘伯温忙用求助的目光看向一旁闭口不言的朱元璋。
“既然是老大两口子的意思,那你就受了吧。”
即便老朱也这么说。
可刘伯温依旧侧着身子,不敢正面接受常氏的三拜。
也是在常氏刚起身的瞬间。
刘伯温表情严肃,庄重整理完衣袍后,冲朱标、常氏恭敬一拜。
“殿下,娘娘,臣刘伯温肝脑涂地,也要拖着这副残躯病体,直到皇孙殿下蒙学的年纪。”
“若天不假年,老臣福德浅薄没有荣幸亲自为皇孙蒙学。”
“臣也愿将毕生心血录之成册,敬献给皇孙殿下。”
“如此便有劳先生了。”
朱标说完看向一旁的太医。
“从今以后,你便留在刘先生府上,一应开销由东宫支应。”
“臣遵旨。”
面对刘伯温那一副受尽礼遇,诚惶诚恐的感激模样。
朱标亲自将他送出了东宫。
可直到走出太子东宫,刘伯温却依旧觉得方才发生的一切有些不太真实。
他本以为召他前来东宫,朱标和朱元璋会一个唱红脸、一个唱白脸,强迫他担任中书丞相,去制衡胡惟庸。
可让他没想到的是。
朱标仅仅是让他给尚未出世的皇孙当老师。
听说过指腹为婚,定下娃娃亲的。
可刘伯温还从未听说过,指腹为师,提前预定好老师的。
和刘伯温一样。
目睹方才发生的一切,老朱虽然不理解朱标为何如此。
但老朱能够确定,朱标这么做,定然有他的理由。
“说说吧,你们两口子打的什么算盘!”
听到老朱的话,朱标轻笑一声,很是坦然说道:
“如父皇所见,拉拢刘伯温。”
“拉拢刘伯温?”
对于朱标这个回答,老朱很是不满。
心中不悦甚至已经写在了脸上。
“臭小子,你是太子,是咱大明将来的皇帝。”
“刘伯温仅仅是个臣子,值得你如此拉拢?”
“你还让常家丫头给刘伯温行拜师礼!”
看着极为不满的朱元璋,朱标轻笑一声,道:
“父皇所言极是,儿子身为太子,自然不需如此拉拢一个臣子。”
“可儿臣真正想要拉拢的,是天下士子之心!”
朱标神情一凛,严肃说道:
“父皇,自从洪武二年的科举之后,朝廷便没有再设恩科。”
“如今我朝中官员的选拔,甚至还沿用先前的察举制。”
“对此,民间早有微词。”
“世家之人更是诽谤父皇您这位朱皇帝轻视文人士子。”
“而那些文人士子没有接触朝堂的资格,自然偏听偏信,听信世家传出的谣言,对您敬而远之。”
听到朱标这话。
老朱冷哼一声,不置可否。
对待读书人,老朱倒是没有太大的偏见。
可对于那些世家大族,老朱是打心底里厌恶。
至于世家大族诽谤自己轻视读书人,老朱自然也是知道的。
之所以没处置他们,只不过是现在还没腾出手罢了。
“所以呢?世家诋毁咱,咱就要给他们让步,求他们不要继续诋毁咱?”
此时老朱眉头紧皱,眼眸之中满是不容置疑的骇人杀意。
“当然不是。”
“给世家让步,他们也配!”
“父皇您应当清楚,刘伯温在士林之中的威望,甚至可以说,刘伯温是天下读书人的精神领袖。”
“儿臣方才如此礼遇刘伯温,正是为了告诉天下士子,朝廷、父皇您,以及儿臣这个太子,对待天下读书人都是格外的优待。”
见老朱眉头微皱,低眸沉思。
朱标话锋一转,继续说道:
“今日朝会时的情形您也看到了。”
“如今我大明朝堂少有敢说真话的正臣,不少官员甚至紧紧抱住胡惟庸这根大树不愿松手。”
“纵然刘伯温的品性世人皆知,可朝堂之上竟无一人敢为刘伯温仗义执言。”
“甚至可以说,你是坐在龙椅上的皇帝,而胡惟庸则是站在百官跟前的皇帝!”
“砰~”
被朱标这么一说。
老朱怒火攻心,一拳狠狠砸在面前的案桌之上。
今日朝堂的景象,老朱也感觉到自己皇帝的权力被胡惟庸这个丞相冒犯。
对朱元璋来说,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。
“的确,如今我大明的官场着实晦暗沉闷了些,所以你打算如何改变?”
见老朱认同,朱标跟着说道:
“官场晦暗,究其根本便是如今沿用察举制推选官员。”
“察举制是不错,将地方有名望、德才兼备的人推举上来,入朝为官。”
“可这些人恰恰是被名声所累,没有锐意进取之精神。”
“他们只有名声,因此他们最在乎的也就只是名声。”
“为了保留这点可怜的名声,这些人便抱团取暖,相互勾结,没有半点锐意姿态。”
“然而科举却是不同,科举上来的学子大多年少,意气风发。”
“凌然少年气,更不愿同官场黑暗同流合污。”
“如今我大明的官场,就是需要这样的新鲜血液!”
对于朱标所言,老朱也很是认同。
“你这是打算重设恩科?”
“不错,儿臣打算今年便重设恩科,举行秋试。”
“一方面,是整顿眼下朝堂晦暗的官场。另一方面,则是为我大明储备官员。”
“储备官员?”朱元璋有些疑惑,低声喃喃。
“父皇,丞相制传承千年之久,你不会觉得只杀一个胡惟庸便能顺利裁撤丞相制了吧。”
“嗯.....”
就在老朱犹豫之际,朱标眼神一凛,沉声说道:
“丞相制传承千年,突然裁撤势必反对声一片。”
“所以儿臣以为,既然要办,索性就办的惊天动地。”
“将来把胡惟庸连同其党羽门客,一并揪出来尽数斩首。”
“只有杀的人够多,才能证明胡惟庸罪孽滔天,才能证明朝廷震怒。”
“只有让天下人看到,胡惟庸这个丞相的党羽遍布朝野,天下人才能明白,父皇您裁撤丞相乃英明之举!”
“也是因此,到时候受胡惟庸牵连的官员定然不在少数。”
“将他们尽数斩首,朝廷官职必然出现空缺。”
“儿臣重开恩科,举行秋试,正是为大明储备人才,弥补官职的空缺!”
朱元璋闻言,心中陡然一惊。
不过让他高兴地是。
此时朱标眼中的果决杀意,竟和他年轻时一般无二。
朱元璋原本还担心朱标过于仁慈,将来恐怕会被朝中大臣欺瞒诓骗。
可现在看来。
朱元璋完全不用担心了。
凭朱标这份果决,就算借给那些大臣十个胆子,他们也不敢诓骗朱标。
更重要的是。
饶是老朱也不得不承认,朱标的目光长远,比他尤甚。
他只想到裁撤丞相时,反对的声音自然不小。
为了平息这股反对的声音,老朱或许也会杀一大片官员。
可他却没考虑到屠杀官员过后,会给朝堂带来官职空缺的问题。
然而这一切朱标都考虑到了。
从方才朱标对刘伯温礼遇有加便能看出。
朱标从一开始,便已经计划好了一切!
“所以礼遇刘伯温,只是你向天下士子证明大明朝堂广纳贤才的手段?”
“正是。”朱标毫不掩饰,直接说道:“刘伯温虽然爵位不高,官位也不过正三品,可他在文人士子中的形象却异常高大。”
“方才儿臣所为,很快便会传遍整个大明。”
“大明太子未出世的孩子拜刘伯温为师,太子妃代为行拜师礼的消息,很快便会在士林之中传为美谈。”
“而儿臣这个太子在士子万民心中的形象,也自然成了礼贤下士,厚待读书人仁厚储君。”
“如此一来,重设恩科之时,前来应试的士子读书人定然再无顾虑,云集影从!”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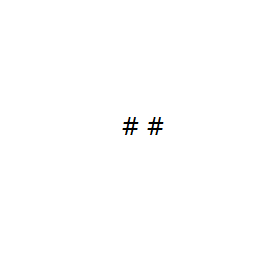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